Copyright © 2022 www.520730.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巴陵时尚网 版权所有 粤ICP备13023037号-1
老毕说了什么(老毕说了什么错话了视频)
- 来源:网络投稿 编辑:爱娱乐小组
2024-01-04 15:34:23
- 关键字:
“星光大道230号”这句话是毕福剑经常说的口头语吗?
不是。《星光大道》毕福剑经常说的口头语是:现场朋友跟我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走人!毕福剑,男,1959年1月生,辽宁省大连市人。曾任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主持的主要节目有《星光大道》、《梦想剧场》、《五一七天乐》等。因其主持风格朴实自然、风趣幽默,常被称作“老毕”。被认为是中国记者进入北极的第一人和央视优秀的主持人之一。扩展资料:《星光大道》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一档选秀节目。节目坚持以“百姓舞台”为宗旨,没有门槛、没有距离,突出大众参与性、娱乐性。力求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一个放声歌唱,展现自我才华的舞台,也是他们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星光大道》播出以来,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百姓歌手。该栏目成功地 推出了阿宝、凤凰传奇、郝歌、李玉刚、杨光、玖月奇迹、刘大成、旭日阳刚、朱之文、金美儿等一大批观众喜爱的百姓歌手。
“…有才有艺你就来…星光大道230号…”绝对是毕福剑经常说的,不过现在不说了,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星光大道230号,其中有奥秘啊!
倒数5个数
不是的呀
“…有才有艺你就来…星光大道230号…”绝对是毕福剑经常说的,不过现在不说了,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星光大道230号,其中有奥秘啊!
倒数5个数
不是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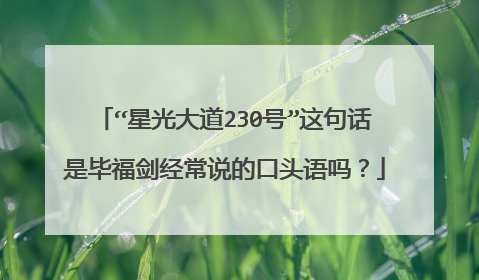
春晚老毕说的恩泽万代,福佑东方如何理解最恰当?
恩泽是恩惠赏赐的意思,比喻恩德及人,像雨露滋润草木。 万代指世世代代,时间久长。福佑是给予幸福和保佑,也指得到的幸福和保佑。东方我想是指中国,咱们一直被称为东方的一条龙。 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给予我们祖国恩德世世代代,像雨露滋润草木一样时间久长,让人民一直得到幸福和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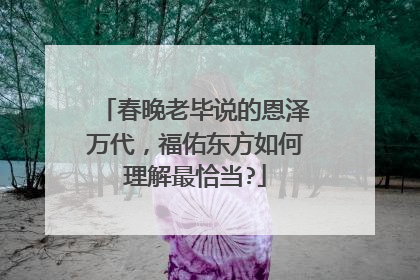
匪我思存<佳期如梦>
<佳期如梦之良辰美景> 是第四部, 第二部是<佳期如梦之海上繁花> ,有连载,不过要在匪的官网注册才能看http://www.feiwosicun.net/viewthread.php?tid=1458&extra=page%3D1刚入行那会儿,杜晓苏曾经听老莫说:“干咱们这行,起的比周扒皮还早,睡的比小姐还晚,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驴还累,在外时间比在家还多,眼比熊猫还黑,头发比鸡窝还乱,态度比孙子还好,看起来比谁都好,挣得比民工还少。”当时听得杜晓苏“哧”一声笑出声来,如今谁再说这样老生常谈的笑话,她是没力气笑了——跑了四天的电影节专题,她连给自己泡杯方便面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到家里痛快洗了个热水澡,拎起电吹风开了开关,结果半天没动静,看来是坏了,她实在没劲研究电吹风为什么罢工,也不顾头发还是湿的,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黑甜无比,铃声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才把她吵醒,拿起手机人还是迷糊的,结果是老莫,火烧火燎的冲她吼:“你在哪里?对面那家拿到了头条你知不知道?”她懵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莫副,我调到娱乐版了。”老莫口齿清晰的告诉她:“我知道你调到娱乐版了,就是娱乐出了头条,颜靖靖出了车祸。”杜晓苏脑子里嗡得一响,爬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夹着手机不依不饶的问:“是那个红得发紫的颜靖靖?”老莫没好气:“哪还有第二个颜靖靖?”杜晓苏素来害怕进医院,尤其是晚上,灯火通明的急诊中心兵荒马乱,她硬着头皮冲进去已经发现了十几个抢先埋伏到位的同行,包括对面那家死对头《新报》的娱记老毕,娱记老毕跟央视的主持人老毕长得一点也不像,娱记老毕长着圆滚滚胖乎乎的一张脸,一笑竟然还有酒窝,此刻他就正冲着杜晓苏嫣然一笑,笑得小酒窝忽隐忽现,笑得杜晓苏心里火苗子腾一下子全窜起来了。“老毕,”她言不由衷笑得比老毕更虚伪:“这次你们动作真快。”“哪里哪里,”老毕都快笑成一尊弥勒佛,语气十分谦逊:“运气好,我正巧跟在颜靖靖车后头,谁知竟然拍到车祸现场,还是我打120叫来救护车,这次真走运,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独家来,嘿嘿,嘿嘿……。”说起车祸来都这样兴高采烈没有半分同情心,杜晓苏于是转过脸去问另一位同行:“人怎么样?伤势要不要紧?”“不知道,进了手术室到现在还没出来。”一帮娱记都等得心浮气躁,有人不停的给报社打电话,有人拿着采访机走来走去,不断有同行接到消息赶到医院,加入等待的队伍,杜晓苏则争分夺秒在长椅上打了个盹,刚眯了一小会儿,颜靖靖的经纪人赵石已经飞车赶到,场面顿时一片骚乱,闪光灯此起彼伏,医院方面终于忍无可忍的开始赶人:“请大家出去,请不要防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老毕嘻皮笑脸:“护士小姐,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看病的。”说着炫耀似的扬了扬手中的挂号单。急诊中心的护士长面无表情:“你是病人?那好,跟我来。”“干什么?”这下轮到老毕发怵了。“看病啊,”护士长冷冷的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众人哄堂大笑,一帮娱记终于被轰出了急诊中心,瑟瑟寒风中饥寒交迫,杜晓苏饿得胃疼,实在撑不下去,于是到医院外面寻了家小餐馆,已经晚上11点,小店里竟然还坐得满满,老板动作慢吞吞的,杜晓苏等了好久才等到自己的一碗鳝丝面。热气腾腾放在她面前,闻着倒是挺香的,待挑起来一尝,鲜!鲜得她几乎连舌头都吞了下去。竟然有这样好吃的面,也许是饿了,她吃得连连嘘气,烫也不怕。吃到一半时电话响了,抓起来接,果然是老莫:“怎么样,搞到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还没有,”她囫囵吞面,口齿不清的说:“人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那赵石呢,他怎么说?”“一大堆人围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医院就把我们全轰出来了。”老莫气得七窍生烟:“他不说你就不会想点办法啊,美人计啊,还用我教你?”杜晓苏自顾自吃面,十分干脆:“好,回头我就去牺牲色相。”老莫拿她没办法,“嗒”的将电话就挂了。杜晓苏随手将手机撂在桌上,继续埋头大吃,这样的角度只能瞥见对面食客的暗蓝毛衣,这种暗蓝深得像夜色一样,她最喜欢,于是从筷子挑起的面条窄窄间隙中瞄过去,看到格子毛衣领上的脖子,再抬高点,看到下巴,还有微微上扬的嘴角,仿佛是在笑。是啊,半夜三更对着手机说牺牲色相,旁人不误会才怪。她才没功夫管旁人怎么想,于是垂下眼帘,十分贪娈的喝面汤,鲜香醇美,一定是用鸡汤吊出来的,这么好吃的面,可惜这么快就吃完了。刚刚快步走出小店,忽然身后有人叫:“等一等。”声调低沉悦耳,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定是北方人。回头一看,暗蓝毛衣,在晦暗的路灯光下更像是深海的颜色,是刚刚坐在自己对面那人,他伸出手来,正是自己的手机。1 ~! |6 w9 D" w, Q* l: z8 _该死!这记性!她连忙道谢,他只说:“不用谢。”正好身后马路上有车经过,车灯瞬间一亮,照得他眉眼分明,咦,真真是剑眉星目,十分好看。杜晓苏对帅哥总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好友邹思琦问她为什么要改行当娱记,她眉飞色舞:“成天都可以看到帅哥,还可以名正言顺的要求访问拍照,多好!”邹思琦嗤之以鼻:“花痴!”其实邹思琦比她更花痴。在医院差不多熬了大半夜,回报社打着呵欠赶稿子,全靠咖啡提神,再花痴也没劲头。老莫还跟催命一样:“下午去医院,一定要拍到颜靖靖的照片。”杜晓苏抗议:“医院滴水不漏,怎么可能让我们拍到照片。”老莫压根不理会:“你自己想办法。妈的万恶的资本家。骂归骂,还是要想办法。没有独家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就没有房租水电一日三餐年假旅游温泉邹思琦说得对,这世上最难收集的藏品就是钱。医院果然滴水不漏,保安们尽忠职守,前台也查不到颜靖靖的病房号,护士小姐非常警惕:“我们这里是医院,病人不希望受到打扰。”可是公众的好奇心还有知情权还有她的奖金怎么办?红得发紫紫得都快发黑的颜靖靖车祸入院,几乎是所有娱乐报纸的头条,老毕的独家照片功不可没,据说《新报》头条的车祸现场照片,令得不少“颜色”痛哭失声,销量一时飙翻。什么时候让她逮到一次独家就发达了。在医院耗了差不多一个下午,仍旧不得其门而入,正怏怏的打算收工回家,结果看到老毕。他鬼鬼祟祟冲她招手。不知道他想干嘛,杜晓苏刚走过去,就被他拖到角落里,笑得很奸诈:“晓苏,我们合作好不好?”叫得这么亲热,杜晓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毕说:“我知道颜靖靖眼下在哪间病房,而且我有法子让你混进去,但拍到照片后,我们一人一份。”杜晓苏生心警惕:“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老毕忍不住长吁短叹:“我也想啊,可惜我是男人啊。”说着打开手中的袋子,露出里面的一套护士服。杜晓苏觉得很搞笑,在洗手间换了护士制服,然后又戴上帽子,最后才是口罩,对着镜子一看,只有双眼睛露在外头,心里很佩服老毕,连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医院很大,医护人员来来往往,谁也没有注意她,很顺利就摸到了二楼急诊中心,老毕说手术后颜靖靖人还在急诊ICU,并没有转到住院部去。结果别说ICU了,走廊里就有娱乐公司的人,两尊铁塔式的守在那里,盯着来往医护人员的一举一动,瞧那个样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别说拍照,估计连只苍蝇也飞不过去。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认命地拖着不甘心的步子往外走,突然脑中灵光一现,掏出老毕画的草图端详了半晌——是真的草图,就在巴掌大的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用铅笔勾出来的示意图,歪歪斜斜的线条像蚯蚓,用潦草的字迹注明着方位,看得杜晓苏差点抓狂,但就是这么一张图,也令她看懂了。消防通道正好紧邻着颜靖靖目前所在的ICU病房。她从消防通道出去,运气真好,ICU的落地玻璃正对着室外消防楼梯,爬到楼梯上掏出相机,可惜角度不行,没敢带庞然大物似的长焦镜头进来,靠相机本身的变焦,根本拍不到。真是功亏一篑,她不服气,看到墙角长长的水管,突然灵机一动。大太阳下水管摸起来并不冰冷,只是有点滑,也许是她手心里流了太多的汗,她艰难的一脚踩在了管道的扣环上,一手勾住管道,这样扭曲的姿势竟然还可以忍受——终于腾出一只手来举起相机。角度好得几乎不可思议,耐心的等待对焦,模糊的镜头里终于清晰,她忽然倒吸了口气,那样深遂的眼睛,剑眉飞扬英气,只能看到口罩没有遮住的半张脸,可这半张脸俊美得不可思议,他穿着医生的白袍,就站在那里,高且瘦,却令她想到芝兰玉树,深秋的阳光透入明亮的玻璃,淡淡的金色光斑仿佛蝴蝶,停栖在他乌黑的发际。杜晓苏刹那间有点恍惚,仿佛是被艳阳晒得眩晕,连快门都忘了按。而他定定的透过镜头与她对视,她只听到自己的心跳,怦怦怦怦怦,一声比一声更响,在一瞬间她突然认出他来,是昨天在小面馆遇见的暗蓝毛衣,而耳朵里有微微的轰鸣,仿佛是血管不胜重负,从心脏里开始漫延膨胀。很奇异的感觉,仿佛是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她才回过神来。而他已经大步冲到了窗边,她胡乱的举着相机拼命的按着快门,然后飞快的爬回消防楼梯,但还是迟了,他迅速的出现在楼梯间,正好将她堵在了楼梯上。杜晓苏无法可想,只好微笑。他看起来似乎很生气:“你在干什么?”杜晓苏一眼瞥见他胸前挂的牌子:“神经外科,邵振嵘” 神经外科?那是什么医生?难道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急中生智还记得满脸堆笑胡说八道:“邵医生——我暗恋你很久了所以偷偷拍两张你的照片,你不介意吧?”

说的对呀 2012春晚是哪个小品里的台词
相声《奋斗》曹云金 刘云天 曹云金:《西游记》台词我熟,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台词也不多。刘云天:您说说。曹云金: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要妖精抓走了,大师兄,我被妖精抓走了。没什么词,师傅,大师兄说得对,师傅,二师兄说得对,师傅,没什么词儿了。师傅,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得对,没有了。放心吧,师傅,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元宵晚会,董卿给朱军和老毕两个人侃的调皮话。“朱军说得对啊!老毕说得对啊!朱军和老毕说得对啊!” 然后这句话就亮了!
沙僧的台词基本就是如此“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啊;二师兄,大师兄说得对啊;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说得对啊;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得对啊” 确实这沙僧的台词说的对啊!!!基本就是这几句 哈,昨天的元宵晚会证明了观点
2012春节联欢晚会-相声:《奋斗》曹云金、刘云天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nxKi-OLjDs/
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5.师傅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5.师傅~大师兄说的对 6.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 7.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 8.师傅,不能赶大师兄走啊!
相声《奋斗》!
沙僧的台词基本就是如此“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啊;二师兄,大师兄说得对啊;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说得对啊;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得对啊” 确实这沙僧的台词说的对啊!!!基本就是这几句 哈,昨天的元宵晚会证明了观点
2012春节联欢晚会-相声:《奋斗》曹云金、刘云天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nxKi-OLjDs/
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5.师傅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5.师傅~大师兄说的对 6.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 7.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 8.师傅,不能赶大师兄走啊!
相声《奋斗》!

冯俊科的文章《鸦雀无声》是什么性质的文学作品
中篇小说 原载《中国作家》2014年第7期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原载《中国作家》2014年第7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8期》转载鸦雀无声1听说市场上卖的一些西红柿又红又大,都是用药物喷洒出来的,不是绿色食品。我有些不相信。正好院子里有块空地,就想自己种绿色食品西红柿。市农科院的高级工程师老毕是我的高中同学,便打电话告诉了他。几天后,老毕笑盈盈的来了,提着一个纸箱,打开看是一箱西红柿秧苗。老毕说:这是刚刚培育出来的,是最好的品种。秧苗栽下后,果然长势良好。到了该结果时,棵棵都结出了西红柿。可后来发现,那些西红柿长得太慢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太大变化。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长的太大,颜色也只是绿中泛些粉红色,不是太红,不好看。这是什么新品种?我打电话给老毕:你是骗我还是把品种搞错了?这样的西红柿怎么能是优质品种?老毕问:你是嫌西红柿长得太慢了?我说:这样的长势,再过两个星期就该下架了。老毕听完笑了,说:这好办。老毕来了,从包里拿出三瓶化学药液。他打开瓶盖让我闻。一瓶有股扑鼻的清香,一瓶酸烈呛人,还有一瓶散发出恶臭。老毕把三瓶化学药液分别用三盆水兑好。一盆水浇到西红柿根部,一盆水喷洒在西红柿枝叶上,另一盆水喷洒在西红柿上。然后对我说:三天后这些西红柿就可以摘了。我问老毕:这些化学药液有毒吗?老毕说:倒进嘴里喝,肯定不行。第二天清早,我起床一看,奇迹真的出现了。西红柿苗变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西红柿个个像气吹似的,长大了许多。又过了一个夜晚,西红柿变得又红又大,色泽艳美,鲜红欲滴。看着这些魔术般出现的西红柿,我吓得有些发毛,赶紧打电话问老毕:这西红柿敢吃吗?老毕说:别人都在吃,你咋不敢吃?我放下电话,看着那些又红又大的西红柿,想着老毕的话,心里直犯嘀咕:这些用化学药液三天长大的西红柿,真的敢吃吗?这篇文章刊登在《新农科技报》上。清晨,司马槐抄起这份报纸准备铺在篮子里去枣树林里拣枣,就在拿起来的那一瞬间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坐在院子里的石磙上,一字一句的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心里像一锅滚烫的开水:吃这些三天长大的西红柿,不就是在吃那三种化学药液吗?现在有些人咋疯了?最好吃的辣椒里兑有苏丹红,最好喝的牛奶里兑有三聚氰胺,雪白的蒸馍都是用硫磺熏的,蓬松焦黄的油条里兑有洗衣粉,最瘦的猪肉里有瘦肉精,最好喝的酒里兑有敌敌畏。用剧毒农药1059浇韭菜,韭菜长得肥嫩厚实,产量很高。还有邻村焦郎庄,一直被誉为市里的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可听知情人说,他们种的蔬菜都是在夜里偷偷喷洒剧毒农药。越喷洒剧毒农药,蔬菜就越是长得叶肥色绿,连一个虫眼也没有,城里人看着就越喜人。话说回来,这些化学东西的神奇效应农民们哪会知道?还不都是那些被称为科学家或专家的人发明创造出来的?那些所谓的科学家或专家们的脑筋是被驴踢了还是钻进了邪风,竟然去发明出这么神奇的化学物品来?看来,有些好看好吃的东西可能更害人,温水煮青蛙,笑里藏刀,软刀子杀人。司马槐觉得自己手有些发抖,心在快速的跳动,脸上冒出了一层虚汗。他想起了自己家的那片枣树林。几十年来,枣树林的那些枣儿在不经意间也发生了奇异变化,这种奇异变化与用化肥厂的肥水浇灌有没有关系?司马槐家的枣树林在湨梁村南面,那是他家的老财院。老财院里长着19棵枣树。爹活着的时候,每年一到冬天,爹就催促司马槐到枣树林培植枣树。司马槐挥镐舞锹的在一棵一棵枣树根部刨出圆坑,“吭哧吭哧”地挑来一筐一筐的猪粪鸡粪和一担一担的人粪尿,埋进坑去。到了春天,他挑来一担一担的井水浇在枣树的根部。爹拄着榆木拐棍站在旁边看,嘴里唠叨说:冬春培植好,秋天结大枣。其实,那时候枣树上结的枣也不大,也不太多。那19棵枣树品种不同。9棵是甜枣树,结的枣儿不大,圆溜溜的,咬一口嚼在嘴里,脆生生甜滋滋的,像灌了口蜜一样。3棵是酸枣树,结的枣儿小,像小拇指头肚,成熟时是乳白色。那枣儿小归小,可味道酸烈,像裹着一包烈醋,轻轻咬一口,酸得满口流酸水,吃两口能酸倒满嘴牙。村里一些怀孕妇女扛着圆鼓鼓的肚子,常到这几棵树下钩枣吃。还有7棵是灵宝枣,个儿大些,椭圆形,酸里带甜,甜里带酸,酸甜酸甜的。收枣时,爹在一根长竹竿上绑一个木头钩,用木头钩钩住枣树枝轻轻摇晃,大枣噼噼啪啪的跌落下来,掉在枣树下像地毯一样柔软的草地上。司马槐那时年轻,性子急,举着钩子钩住枣树枝死劲摇晃,没有揺几下,木头钩“咔嚓”就被掰断了。司马槐埋怨爹:“铁钩结实,为啥不让用?非要用木头钩。”爹说:“铁钩结实,死劲摇晃,还不把枣树摇晃死了?恁老祖爷说,枣树怕铁钩,摇晃树会疯荒。用木头钩揺晃,越揺树越旺。”枣树顶部有钩不到的枝,爹叫司马槐爬到树上,抓住枣枝摇晃。剩下一两小枝时,爹就说:“不要揺了,留着吧。”看着挂满枣儿的枣枝,司马槐说:“我费劲扒拉爬上来,干啥要剩两枝枣不揺?”爹说:“留给鸟吃。”司马槐问:“鸟有啥功劳,留枣给鸟吃?”爹说:“啥功劳?树上的虫不是鸟吃的?没有鸟,虫把枣树吃死了,你还能吃上枣?”后来,爹去世了。爹去世的第二年,村里从县化肥厂引来了肥水,自从用上了肥水浇枣树,上粪浇水那些繁重的活儿就彻底不再干了。费力流汗的活儿不干了,可每年大枣结的比爹活着的时侯任何一年都格外多,长得也格外好。看到不费力气年年丰收的大枣,司马槐的感觉就像爹当年被共产党从旧社会的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轻松和喜悦。啥叫肥水?其实是废水,就是从县化肥厂排出来的废水。那废水从化肥厂合成车间、蒸馏车间、冷却塔包括从化肥厂工人洗澡的澡堂里流出来,说是含有很多化肥残留。化肥厂长老狄说:这些废水是地地道道的肥水,用来浇地,不用再上化肥,不用再上底肥,也不用再上人粪尿,庄稼长得壮实,亩产能达八百至一千斤。他还编顺口溜说:“肥水是个宝,庄稼离不了。一年浇三遍,不用上肥料。”肥料对种庄稼的农民来说,就是多打粮食的法宝。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有了肥料庄稼就能长得好,打得多。当时的湨梁村地多贫瘠,盐碱地沙土地胶泥地料礓地多,没有肥料,庄稼就像营养不良孩子,长得稀稀拉拉,病恹恹的,遇到旱涝虫害,种100斤种子,只能收获80多斤,收的没有种的多。为了改良土壤,多打粮食,庄稼人一年四季,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积肥。人粪尿不够,政府就号召群众多养猪,说养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厂。提起养猪积肥,司马槐的心里就翻腾着说不尽的苦水。司马槐家养了五头猪。炎热的夏天,太阳火烧火燎的烤着,司马槐钻进齐腰深的玉米地割青草,玉米叶子把身上拉的青一道紫一道,汗水浸泡着,火辣辣的难受。割完青草捆成捆,背着一大捆死沉死沉的青草回到家来,扔进猪圈里,担两担清水往青草上泼。猪吃了泼水的青草拉的屎就稀,拉屎也快。还有些草猪不吃,就往上面撒一层土,泼上水,猪在上面拉屎撒尿踩和,沤上几天就成了猪粪。出猪粪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司马槐跳进猪圈,挥舞着三刺耙,把猪踩实沤好的粪一大块一大块的劚﹙音zhǔ,砍、斫的意思﹚松了,再用铁锹一锹一锹铲起来的扔出猪圈外面。猪圈里屎尿遍地,腥臊烂臭,呛得肚子里一鼓一鼓的直想呕吐。用三刺耙劚猪粪时,那五头猪也不老实,它们开始时拥挤在一起,瞪着十只猪眼惊恐地看着司马槐,拱着猪嘴唧唧的叫唤,后来就满圈的奔窜跑跳,猪身上带的稀泥屎尿,溅的司马槐腿上身上脸上脏兮兮的。有一次,司马槐举起三刺耙狠劲地劚下去,没有料到一只小猪跑过来,正好钻到三刺耙下面,一耙不偏不倚地劚在小猪头上,小猪四蹄伸直,浑身颤抖,眼睛翻白,唧唧叫唤两声就没有气儿了。司马槐抱着死去的小猪,心疼的流出来眼泪,有好几天坐卧不安。猪粪出圈后,再用三刺耙把大块的劚成小块,小块的劚碎,敲打成土状。用两只箩筐装满猪粪,一担一担的挑到几里地远的庄稼地里。一担猪粪足足有一百多斤,出一次猪粪要担上好几天才能担完。猪粪担到庄稼地,回来时箩筐不能空着,还要在路沟里担满满的两箩筐土,撒到猪圈里,重新开始下一次积肥。司马槐恨透了弄猪粪。化肥是啥东西?祖祖辈辈的湨梁村人只知道肥料,就是能够肥地的人粪尿猪鸡粪,从灶台里掏出的草木灰,还有拆除百年老房的墙土,从来没有听说过啥叫化肥。司马槐第一次知道化肥,是大队长老山通过县供销社当副主任的二爷弄来的一小袋日本尿素。那日本尿素装在绵软结实的塑料编织袋里,封口的地方有一根线,老山在众目睽睽下搓了搓手,像拉手榴弹拉环一样,捏着线头“嚓”地一拉,口袋就开了。里面露出一粒一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洁白晶莹,在太阳下泛滥着光泽。司马槐正好赶到了,他嘴里“啧啧啧”的直响,说:“这老日本的米咋恁白?”伸手抓几粒放进嘴里,立刻跳了起来,喊:“我操,这老日本米咋苦嚓嚓嚓的,蜇得满嘴像火烧?”老山说:“你真是个憨囟球。这是日本化肥,给庄稼上的,你知道吗?。”司马槐说:“不知道。”老山说:“是化—肥—,就是用化—学—做成的肥料。”老山一脸的傲气,故意把化和肥、化和学两个字分开,把它们的音节拉长。一提老日本,提起化学,司马槐的心里打了个激灵,立刻警觉起来。他说:“老山,这是老日本用化—学做成的肥料?”老山说:“那还有错?你看看这袋子上写着:尿素,日本株式会社。”司马槐说:“老山,你不知道老日本的化学厉害?”老山瞪着司马槐,问:“老日本的化学厉害,你啥意思?”司马槐说:“当年,老日本在县城俺连种他姥姥家,扔过一个化学炸弹,他姥姥、姥爷和街坊邻居十几家几十口人身体溃烂,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一年多后全死光了。到现在那些院子还草木不生,蝇虫绝迹,没有人敢住。这些你都忘了?”老山脸色如水,没有吭声。司马槐说:“现在老日本又弄化学做成肥料,用这化学东西上到庄稼地里,到底是好还是坏?打的粮食会不会把人吃成聋子瞎子和哑巴?会不会把人吃死?你敢保证?”司马槐的话像炸弹,炸得湨梁村人哑巴了一样,都没有吭声。老日本当年用化学弹造成的那种危害、那种惨状,全村、全县20多岁以上的人,谁不知道啊?既然是老日本用化学做的肥料,那就看看吧。老山提起那袋日本尿素,悻悻而去。当大家还是像祖祖辈辈那样,“嗨吆嗨吆”的挑着猪粪或人粪尿往庄稼地上的时候,人家老山已经从繁重脏累中解脱出来了。他欢快的吹着口哨,轻轻松松地抓上几把日本尿素撒在小麦地里,结果是小麦比全村长得都好。靠着路边的打麦场上,老山把小山一样的麦籽堆放在路边,他在麦籽堆上插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毛笔写着醒目的字:“日本化肥好,亩产860斤。”小山一样的麦籽堆,老山一直堆放了好几天。听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才赶紧把麦籽收进了仓库。湨梁村人激动起来了。院里院外,前街后街,田间地头,人们嘴里都在交口称赞:“妈那ⅹ,这老日本的化学肥料咋恁厉害?一亩地产量比两亩地还多。”“我操,早知道咱也去弄袋日本化肥用用。”老日本的化学肥料厉害是真厉害,但不是谁说想弄就能弄到的。那化学肥料太金贵了,一袋日本进口的化肥要35块钱。也非常不好买,筹够了钱没有后门也根本买不到。庄稼人没有别的念想,一天到晚都念想着咋样才能让庄稼长得好,能够多打粮食。面对化学肥料的诱惑,司马槐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在饭场对大伙说:“咱三家五家的凑钱,找老山他二爷合着买一袋化肥,回来后再分咋样?”就这样,湨梁村开始有人一袋一袋的扛回了化肥。有了化肥,上的方法也讲究。要用手一小撮一小撮的捏着,精心的丢到离庄稼的根部四指远的地方。太近了不行,肥力太壮,会把庄稼烧死。太远了也不行,天气热挥发快,会失去肥力。有一省心就有一费心。上完化肥就不像上完农家肥,要不分昼夜的赶紧浇水,浇水晚了蒸发的氨气会把庄稼叶子熏干枯死。为了及时给上了化肥的庄稼浇水,也真是累死了人。浇水用的辘轳是汉代传下来的。一个三尺多高的梯形辘轳架上,架着一个直径一尺左右、七尺长的的圆筒,圆筒的两头朝相反方向缠绕着两根牛皮绳,牛皮绳上挂着两个大水桶。辘轳架两头站着两个人,绞动着辘轳把,两只大水桶一上一下的从井里把水绞上来,倒进水池里,水就顺着小水沟慢慢向地里流去了。两个壮劳力用辘轳浇地,挥汗如雨,腰弯酸了,手磨出茧子,一天也浇不了半亩地。土井不够用,不到半年时间,湨梁村的田野里新打了二十几眼土井。县里要建化肥厂了。化肥厂是专门生产化学肥料的工厂。有了化肥厂的肥水那该有多好?不用割草背草挑水沤猪粪,不用跳进腥臊烂臭的猪圈里劚猪粪,不用掏钱求人买化肥,不用钻在庄稼地里用手一撮一撮的丢化肥,更不用扭屁股弯腰地摇着辘轳把去浇地。肥水沟一年四季打地头流过,肥水里既有化肥又有水,庄稼想啥时候浇就啥时候浇。不费力气,也不用掏钱买化肥,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后来的现实告诉了湨梁村人:老狄的话一点儿没错,那肥水可真是神水。就像那神奇的化学药液能让西红柿三天长大一样。庄稼每年浇上三遍,啥肥料也不用再上,也不用累死人的辘轳浇水,小麦玉米谷子穗大粒饱满,年年丰收。就连枣树林里的老枣树,每年浇上两遍肥水,便像焕发了青春一样,枝壮叶绿,也不再长虫了,枣儿结得也格外多、长得格外大,个儿大饱满,色泽鲜亮,一嘟噜一嘟噜的,把枝条压得像村西头的老罗锅一样,弯得直不起头来。司马槐经常扯着五音不全的嗓子,学着豫剧《李双双》里的喜旺唱:“庄稼人有哇了它,可是真得法啊……”提起大枣,司马槐突然想起了前几年卖大枣的事。司马槐拉着一架子车的大枣在街上卖,一个怀孕的女人说:“买点小酸枣。”他拿起一个枣递过去,买枣的女人咬了一口嚼了嚼,说:“你这是啥狗比掰酸枣?寡甜淡酸、苦不拉叽的。”司马槐又拿一个递过去,那女的咬了一口嚼了嚼,“呸呸呸”地吐到地上,说:“咋都是一个味儿?”扔下半个枣气哼哼的走了。司马槐自己拿起几个枣咬在嘴里嚼了嚼,果然像那个怀孕女人说的,都是一个味儿。要是在夜里吃,凭品味道肯定猜不出吃的是大枣。他突然发现,本来形状不同、品种分明、味道各异的甜枣、酸枣和灵宝枣,这些年长得咋都是大大的?圆圆的?一律的紫红颜色?大的有些可怕,圆的有些出奇,颜色就像嫩紫皮的茄子。哪些是甜枣、酸枣和灵宝枣,味道全都差不多,也分不清了。吃在嘴里就像嚼蜡,一点也没有枣的味道。这是不是肥水里那些化学的东西造成的?近这几年,大枣虽然年年丰收,可连司马槐自己和家人也不爱吃枣树林的枣了。他曾给老山说起过枣的神奇变化,老山说:“肚饥吃糠香,饱了肉当糠。现在的人是肚里油水大了,嘴变刁了。” 司马槐又想到了用化学药液三天催大的西红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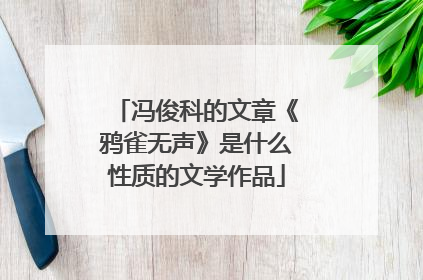
相关阅读


















